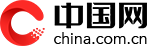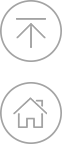朱鳳瀚《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竹簡〈詩〉初探》(《文物》2020年第6期)對海昏侯墓出土《詩》本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,使我們對海昏侯《詩》簡的價值有了初步的認識。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有1200枚《詩經》簡,雖然多為殘斷簡,但數量如此大的《詩》簡對我們討論漢代《詩經》學相關問題意義重大。具體說,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:
第一,關于《毛詩》與三家《詩》本差異的問題。漢興之初,書簡殘斷,經學文本多為再造文本。劉歆于《讓太常博士書》說,“至孝文皇帝……《詩》始萌牙……至孝武皇帝,然后鄒、魯、梁、趙頗有《詩》《禮》《春秋》先師……當此之時,一人不能獨盡其經,或為《雅》,或為《頌》,相合而成……時漢興已七八十年,離于全經,固已遠矣。”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,漢代《詩》本是統一的文本嗎?或者說,《毛詩》與三家《詩》本差別大嗎?
以往囿于材料,我們只是知道三家《詩》本的一些零星材料。根據這些材料,學者判斷《毛詩》與三家《詩》的差別不大。今據海昏侯《詩》本可知,《毛詩》與三家《詩》差別還是比較大的。比如分卷的不同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《毛詩》二十九卷,而三家《詩》本二十八卷。它們之間的一卷差異何在,清儒王引之、王先謙都有各自的解讀。對照海昏侯《詩》看,不論是王先謙將《邶》《鄘》《衛》三詩合卷還是王引之以《周頌》三十一篇當一卷,都不正確。不僅如此,根據朱文可知,海昏侯《詩》分為二十九組,亦即二十九卷。這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《毛詩》經文卷數相同,和魯、齊、韓三家二十八卷經文不同。推其緣由,或是我們對簡文分組的解讀有誤,比如《魯頌》《商頌》篇數較少被合為一組,是否《曹風》《檜風》也被合為了一組?抑或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有誤,是否魯、齊、韓三家《詩》本也是二十九卷而《漢志》誤記?又或是海昏侯《詩》本是西漢早期的《詩》本形態,劉向整理圖書可能又對三家《詩》本做了調整,二十九卷遂變為二十八卷。而相對于分卷,分章的差異更大。海昏侯《詩》本章數為1076章,而《毛詩》為1149章,比海昏侯《詩》本多73章。但總句數二者相差不大,《毛詩》多21句,多出的21句大概便是類似《都人士》首章之類。具體到細部,依照推算可知,海昏侯《詩·小雅》只有299章,比《毛詩·小雅》少68章,但句數至少要多100句。海昏侯《詩·風》章數和《毛詩》相同,但句數至少要少120句。這些具體的差別不僅是編排方面,比如詩篇的排序、章節的劃分,也包括文本內容,尤其是文字和句數。或許待海昏侯《詩》簡全部公之于世,我們會有更深入的認識。
朱鳳瀚先生認為海昏侯《詩》屬于《魯詩》,這一結論或仍有商討的余地。無論海昏侯《詩》是否為《魯詩》,謂之屬于三家《詩》當無大礙。孔穎達說:“《詩》體本是歌誦,口相傳授,遭秦滅學之后,眾儒不知其次。齊、韓之徒,以《詩經》而為章句,與毛異耳,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。”由此可知,漢儒既各自再造《詩》本,又無舊《詩》本可參,故所造《詩》本各異。然魯、齊、韓既然同立于學官,《詩》本自當經過統一。漢代《毛詩》不立于學官,與三家《詩》自然不屬于同一系統。
第二,關于三家《詩》本關系問題。根據現有的材料判斷,三家《詩》本在詩篇數、編排、分章等方面應該保持較高程度的一致性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“經二十八卷,魯、齊、韓三家”,其言下之意即謂三家《詩》經的內容及編排具備一致性,文字或有差異。如果僅僅是卷數一致,經文內容及編排差別較大,當不至于如此表述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“《孝經》一篇。十八章。長孫氏、江氏、后氏、翼氏四家”,《孝經》類序記載長孫氏、江氏、后氏、翼氏等“經文皆同”。可為旁證。而比較《韓詩外傳》引詩次序、海昏侯《詩》以及熹平石經《詩》的詩篇編次,也可發現它們幾乎一致。如《韓詩外傳》卷六引《詩》皆為《大雅》,其篇序為《抑》《桑柔》《瞻卬》《假樂》,和海昏侯《詩》中這幾首詩的排序相同,也和石經的排序相同。但是在《毛詩》中,《假樂》屬于正《大雅》。事實上,《毛詩》和三家《詩》對正《大雅》詩篇的編排并不一致。服虔注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九年之“為之歌《大雅》”曰:“陳文王之德,武王之功,自《文王》以下至《鳧翳》,是謂正大雅。”對照《毛詩》編次,則服虔所謂“正大雅”蓋自《文王》至《鳧鷖》,共計十四篇,至少《假樂》《公劉》《泂酌》《卷阿》等四篇不在其中,此正可與海昏侯《詩》、熹平石經相互印證。對照海昏侯《詩》,知《行葦》亦不在三家“正大雅”之列。但熹平石經殘石無《行葦》信息,故難以舉證。關于《行葦》詩旨,《毛詩序》謂之“忠厚也”,但《列女傳·晉弓工妻傳》、班彪《北征賦》、王符《潛夫論·德化篇》《吳越春秋》以及《后漢書·寇榮傳》等皆以為是公劉詩。既然三家《詩》學《公劉》不在正《大雅》之列,《行葦》不在其中也在情理之中。最后,漢人常以“三家《詩》”如何,以表述與《毛詩》的差異,也可證三家《詩》本為統一之文本。如《都人士》首章,鄭玄注《禮記》曰“此詩,毛氏有之,三家則亡”。而服虔注曰“逸詩”,蓋亦本之三家《詩》為說。據此,清儒所謂“三家遺說,凡《魯詩》如此者,《韓》必同之;《韓詩》如此者,《魯》必同之;《齊詩》存什一于千百,而《魯》《韓》必同之”,雖稍顯武斷,但也并非全無道理。
第三,關于漢代經學“經傳合編”問題。關于漢代經傳的編纂形式,孔穎達曰:“漢初,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,三《傳》之文不與經連,故石經書《公羊傳》皆無經文。《藝文志》云:《毛詩》經二十九卷,《毛詩故訓傳》三十卷。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。及馬融為《周禮》之注,乃云‘欲省學者兩讀,故具載本文’。”根據孔穎達的說法,馬融之前似經傳別行,而馬融之后則經傳合編。但海昏侯《詩》簡經的正文附有詁訓,如“金玉其相。相,狀也”。甚或附傳,如《陳風·墓門》“顛倒思予”,海昏侯《詩》作“……將顛倒思予乎。傳曰:晉大夫解居……(161)……婦人不由其道,為作是詩”。《詩》之外還有《春秋》這讓我們對西漢中期經傳的編纂問題有了新的認識,有學者也據此對孔穎達“經傳別行”說提出疑問,認為《毛詩故訓傳》也當如海昏侯《詩》經傳合編。但這一問題似乎不能一概而論,尤其不能將其絕對化。比如《公羊傳》,漢石經《春秋》確實是經傳別行,而海昏侯墓出土的《春秋》確實經傳合編。我想,不論是別行還是合編,皆以不影響理解經文為首要前提。漢石經《公羊傳》大概會標記“某公元年”以及其下的具體年數,這樣閱讀起來就相對方便。其次也當考慮內容,若內容太少何以成卷?就《詩》而言,雖然海昏侯《詩》簡有注文,但太過簡短。以《檜風》為例,海昏侯《詩》只是對“萇楚”“夭夭”“匪風發”“懷之好音”進行了簡單注釋,并且體例不一。如果這樣的內容單獨成卷,大概書于一二枚簡就足夠了,實在難以成卷。相比之下,《毛詩·檜風》注文有300多字,大約15枚簡左右。所以,我們猜想海昏侯《詩經》中注文大概是劉賀的個人行為,并非漢代《詩》經學之通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《魯故》二十五卷、《齊后氏故》二十卷、《齊孫氏故》二十七卷、《韓故》三十八卷,與經文卷帙皆有不合。如何分合,尚難定論。相比較而言,《毛詩故訓傳》三十卷則比較分明易把握。如果一卷之內的每首詩加上篇題和詩小序,相信《毛詩故訓傳》非常便于使用。這里有兩點需要提醒大家注意,一是《詩》便于諷誦,沒有經文并不會對理解《毛詩故訓傳》產生太大影響。二是鄭玄說《詩序》原本合編,“至毛公為《詁訓傳》,乃分眾篇之義,各置于其篇端”。推想毛公所以將《詩序》“各置于其篇端”不僅有助于理解經文,也是為了標識詩篇,便于理解每首詩的故訓。總之,《毛詩》的故訓傳與經文別行并不會影響使用,孔說不可輕易否定。
漢代《詩》本的流動性較大,今天的所見《毛詩》于劉向整理圖書之后又經多次整理。比如《毛詩》原本《關雎》分三章,而鄭玄分為五章。所以我們今日所見《毛詩》與海昏侯《詩》的不同,也存在較大可能性是鄭玄改《毛》所致。與此同時,我們似乎也不能忽視海昏侯《詩》作為隨葬品的屬性,以及由此導致的文本變形。因而在根據海昏侯《詩》簡等討論漢代文本共同屬性時,當保持一定的警惕性。作者:張玖青(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)
《光明日報》( 2021年08月16日13版)